文 | 车宁
看懂App评论作家(ta已经入驻看懂App小程序,关注他可来看看懂App小程序)
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力量(生产方式的新组合),这种力量能够破坏任何可能达至的均衡。——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是运动着的、永远在“计算”自身的,或者说,经济无时无刻不在重新构建自身。——布莱恩•阿瑟
自吾国步入近世以来,由庚子年开启变革通道似乎已成为新的历史传统,由鸦片战争而五口通商、由辛丑条约而仿行立宪,而今这一逻辑看来仍在继续。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过年气氛的时刻,新冠疫情突然袭来,由一城而一省,进而波及全球。疫情的冲击全面且深刻,不仅是对公共卫生的大考和社会治理的检验,也对社会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作生活秩序造成影响。除了生命和疫情的“热战”外,从更加底层和隐秘的角度看,网络和城市的“暗战”也已初现端倪——在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餐饮、出行等行业叫苦不迭的同时,基于线上消费的网络游戏、在线视频等却赚得盆满钵满,真可谓“冰火两重天”。基于经济史角度的观察,某种商业模式一旦被接受为行为习惯,其路径依赖就会越来越“锁定”,而由锁定带来的惯性甚至不会在后续发展中被“消化”,反而会成长为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本文写作的目的,正是通过对这项由事件而引发趋势的观察,在感性认识之余尝试沉淀下对未来的理性勾勒。

◆ ◆ ◆一、面临收缩的城市
从有记述历史以来,对城市的向往就成为人类共通的文化记忆,不仅有“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这种赤裸的“羡慕嫉妒恨”,也有从“上帝之城”到“极乐刹土”各种对未来天堂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形态毫无例外也是城市的。
没错,正是城市发展了文明、孕育了国家,西方文明的源头是爱琴海畔的雅典、斯巴达城邦,而东亚国家的建构也来自于黄河流域的“大邑商”及“赫赫宗周”。
然而,城市的优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经由一场场历史事件通过“打怪升级”实现了对原始聚落的替代。相较于后者,城市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如工商业等产业形态,能够为贸易提供更大的市场并与其共同成长,能够聚集更多更复杂的人群进而孵化更精巧的生活方式、商业实践乃至制度文明等。
基于技术比较文化的视角,我们也不妨把城市看做前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正是凭借着这种初步的网络优势,自农耕文明以致于工业文明,城市逐渐积聚起各种前人无法想象的势能,终于将我们带到了网络文明的门槛。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伴随着所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弊病也逐渐显露:人口扩张过快、公共服务缺位、贫富分化拉大、环境破坏严重等等。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不同于美国、巴西、澳洲等“新大陆”国家,我们的现代城市主要来自历史城市的改造。
从选址来看,过去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除了必要的自然经济条件外,很重要的就是有可供防守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山川河流,而这些山川河流显然又是城市规模和经济扩展的桎梏。从发展来看,政府有形之手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资源的调配并不完全按照自然条件的优劣展开,城市的诸如经济等职能的承载很多是扭曲的。
在此基础上,由市场规律自发形成的规模作用又在持续加剧之前的“错误”,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在这里竟成了一种黑色幽默和反讽。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我国的城市发展定位有可能重构。长期以来,在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实践之外,其实一直存在着优先发展县域城镇的呼声,过去的代表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江村经济》,如今的表现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争论。
疫情在特大城市的肆虐可能造成这一声音的抬头,一方面城市功能、规模将会与其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限度挂钩,另一方面去中心化、去职能化的探索可能开始,过去集中在区域一个中心城市然后“摊大饼”的做法将会让位于以中心城市分散功能给周围中小城市、城镇的“众星捧月”布局。
另外,在对城市功能收缩的考察中还应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首先,目前我国达到的14亿人口规模很可能是历史峰值,见顶的人口无法进一步支撑城市的扩张;其次,人口的世代交替将会深刻影响经济的组织方式,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90后、00后等“互联网原住民”(特别是其中的“小镇青年”)对城市的认知和对待明显有别以往;最后,从微信聊天到淘宝购物,从今日头条到抖音快手,中老人群对网络行为习惯的学习和接受超出预期,他们本来就因退休而削弱了与城市的联系,而今更被整合至网络经济中而增强了后者对城市的替代砝码。

◆ ◆ ◆二、持续崛起的网络
曾经,城市凭借强大的贸易网络、优越的公共服务、不竭的商业创新打败了所有可能与其竞争的组织形式,而今恰恰在这三个层面都遭遇了网络的全面挑战。
一则,由信息网而资金网,网络编制了比城市覆盖更广、更有效率的贸易体系,并且这个贸易体系还在加速从线上到线下整合旧有资源;
二则,由网络效应而平台效应,网络也拟制出了对多方、异质主体的“准”公共治理,这种治理在效率、公开和参与等方面已初步展示对传统城市治理的优势;
三则,网络能够容纳更多商业模式的成长,这不仅表现为其“复杂性”可以为创新提供更多空间和可能,还表现为由其孕育的创新将一道增加其生态的丰富,甚至表现为对过去非网络资源的捕获和整合。
如果说网络对城市的替代过去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也仅是探索和渐进的,那么此次疫情则给其全面扩张提供了机遇:在消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场景,闭环构建更加完整。“宅”在家中的人们在关注疫情之余,也需要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因此视频直播、游戏娱乐、移动新闻甚至在线教育等都借此机会走出过去相对封闭的消费人群,尽可能扩展场景和内容,成为全民时尚“新宠”乃至主要渠道。

不仅如此,人们对于必须线下消费的特定产品如食品、蔬菜等的需要和“足不出户”的现状还催生了线上线下商业体系的进一步融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促成了经济发展新老动能的交替。
在生产领域,以移动办公为起点,一直不温不火的工业互联网有望取得突破,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真正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同于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的产品提供更多是“定制化”而非“标准化”的,只有满足企业的真实需求,企业才会为此买单。
而当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经营并没有实现线上化、数字化时,企业需求非但无法对接,甚至无法搞清。移动办公的兴起有望打破这一瓶颈,带动整个企业经营的线上化、数字化转型,企业因此能够引入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管理体系和金融产品,促成自身乃至宏观经济的“二次腾飞”。
在政务领域,不仅智慧政务开始深入人心,由政务数据开始的数据共享也将推动相关产业的成长。
一方面,疫情犹如一场大考,暴露出社会管理的一些问题,也使得中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号召更有迫切性,而智慧政务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正是构建完善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完善的治理体系需要立足于数据的公开及共享,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高质量政务数据的开放可以使企业打通数据使用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而这恰恰是最值得期待的动人前景。

◆ ◆ ◆三、因势利导的对策
本质上看,网络对城市替代的背后是技术演进。
一方面,新的技术来自于已有技术的进化和组合,而沉淀稳定下来的技术又作为下一次技术进步的基石,技术本身就构成一个持续正态演进的系统;
另一方面,就如经典经济学家指出的,作为生产力的新技术还会催生与其适应的新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同时尽力挣脱原有机制对其的束缚。从一点一滴的“历史小事件”出发,以技术作为底层逻辑和根本动力的网络经济已汇成滚滚向前的大江大河,其势已成,未来可期。
然而趋势并非当下,历史的替代需要时间的推进。立足眼前,我们有必要再次确认(澄清)三个问题:
第一,城市是收缩而非衰落,其表现是功能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重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丧失比较优势的城市也将不可避免的步入颓势;
第二,网络对城市的替代是作为经济组织方式主导权的替代,网络现在不会未来也很可能不会实现对城市功能的完全替代;
第三,替代是一个过程,其间将会充满博弈甚至反复,决策者在趋势判断之余需要紧密结合事件,保持对策的灵活度。

《周易》有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中性地看,新冠疫情固然是“危”,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机”,事实上,从非典以来的每一次公共事件都催生了网络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关键在于因时而变,变则通,通则久。至于具体的对策层面,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最可着手的都是产品工作。
对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来说,首先需要树立和坚定城市运营者的意识,城市运营不仅仅是招商引资,现在和未来仅凭财税政策让利无法实现企业入驻和经济成长,关键是提升公共产品的内容和方式,从健康、环保、民生、企业服务等各个领域以全方位的治理能力打造本城市的比较优势。
对于企业来说,网络的崛起首先提供了一种替代方式,可以两条腿走路部署经营,在此基础上要围绕产品做细经营战略,以网络、网络经济生态、网络消费人群为出发点有机结合自身积累和特色,有取舍地安排产品的定位、研发乃至于前端营销布局和后台运营组织。


财经自媒体联盟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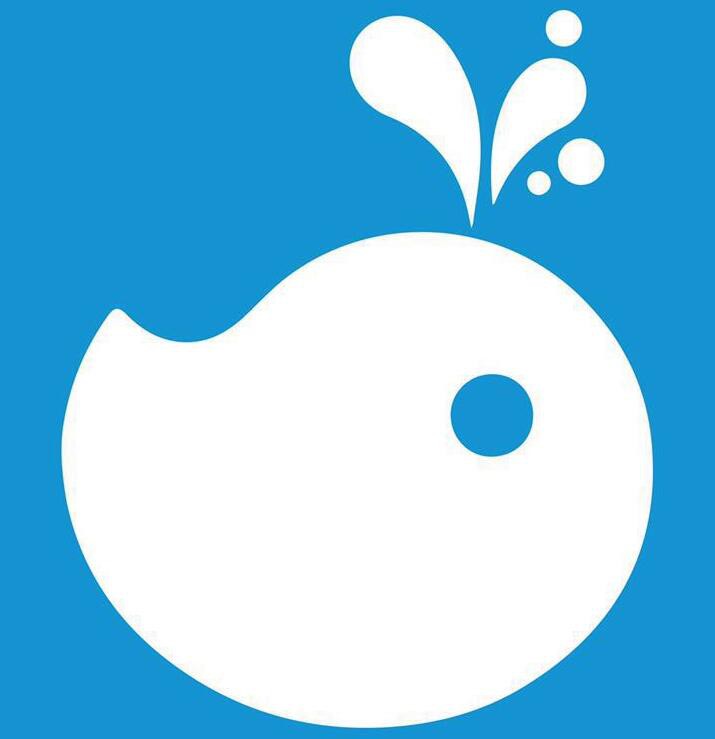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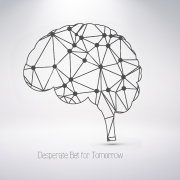






















 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财经日报  每日经济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贝壳财经视频
贝壳财经视频  尺度商业
尺度商业  财联社APP
财联社APP  量子位
量子位  财经网
财经网  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